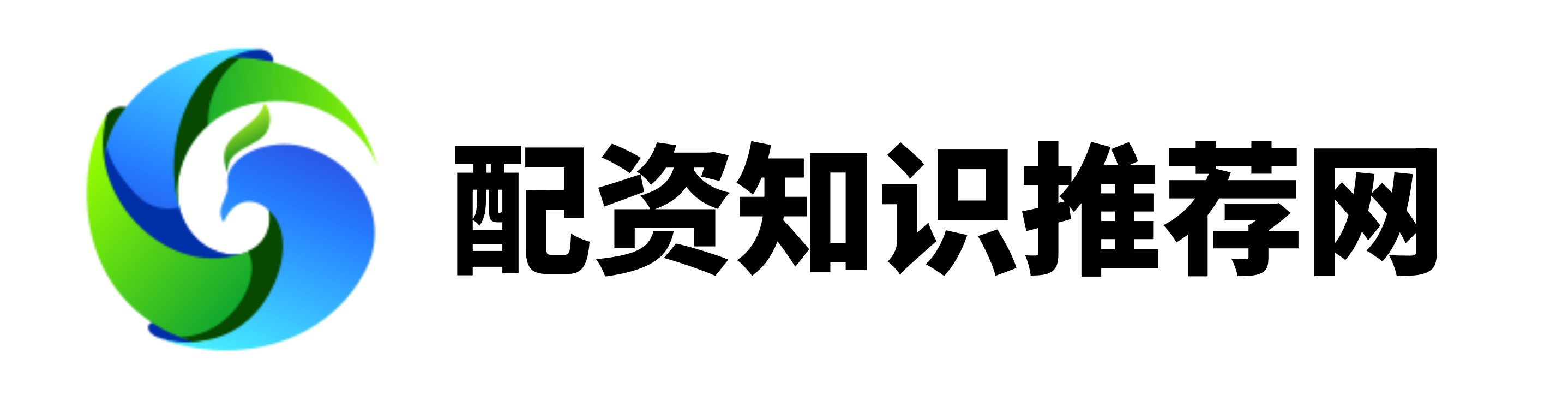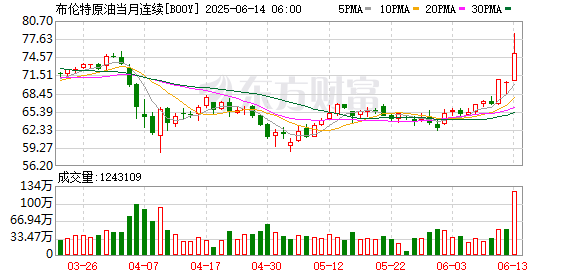炒股配资网站 庆功会上黄百韬悲叹:25军被粟裕耗尽元气,我过不了50岁大关

“1948年11月7日晚上炒股配资网站,新安镇,黄百韬盯着地图嘟囔:‘这仗要这么打下去,我连五十岁都撑不到!’”侍从参谋听得心头一跳,却不敢接口。短短一句话,折射出一个前线兵团司令对未来的深深绝望。

庆功酒桌就在隔壁。顾祝同南来徐州,专门给黄百韬贺勋。按说,豫东战役救援区寿年有功,青天白日勋章已挂在胸前,再加上第七兵团司令的权柄,黄百韬理应意气风发。可推杯换盏之间,他突然苦笑:“勋章能当盔甲吗?我只怕天命难过。”众人一时语塞,场面冷了半分。顾祝同知道这位旧部的心结,却也只能以几句“休要多虑”来敷衍。
黄百韬的阴霾并非源于一时疾病。他清楚,七兵团眼下驻碾庄圩,西有徐州“剿总”调度混乱,东有粟裕华野锋芒逼人,前路后路都不稳。“一条运河、一座铁桥,就是全部退路,”他反复念叨,“要是再耽搁一夜,怕是兵也救不了,命也保不住。”众幕僚听得胆寒。事实上,迟来的四十四军正拖着七兵团原地等待,关节就在这两天延误。

时间回溯七年。1941年皖南事变,新四军主力突围受阻,25军封锁要道,叶挺被扣,袁国平被害,这一笔血债黄百韬心知肚明。那时他仅是参谋长,接过军旗后,深感“杂牌”出身抬不起头,便铁腕治军,夜训、山地渗透、沼泽进击样样狠抓。官兵暗地里给他起外号:“焕然军长”,既佩服也畏惧。
抗战末期到内战初,25军扩编为整编二十五师。设备精良、番号响亮,可首次与粟裕交锋的苏中七战,他就发现自己拿老一套阵地战根本防不住对面的“钉子战术”。粟裕三个纵队像拳头一样在水网地带闪展腾挪,国军后勤和通信却被割得七零八落。兵力明明占优,却步步被动,黄百韬自嘲“拳击手打不过影子”。
1947年孟良崮,张灵甫孤军突入,黄百韬奉命护左翼。双方第一次通话时,张灵甫蔑然一句:“老黄,你那两旅的脚程,可别掉链子。”黄百韬心里窝火,却不敢赌命狂进,结果粟裕抓住他一丝犹豫,天马山被顶死,包围圈闭合,七十四师灰飞烟灭。战后,蒋介石痛斥“不勇不忠”,黄百韬被记过,心理的裂痕由此加深——他开始相信“粟裕能看穿人心”。

豫东战役的“黄泛区大捷”,表面上给了黄百韬一口气。可他最清楚:那一役自己的25师三天损失师部直属两个团,若非粟裕久攻开封而分兵,他早被榨干。勋章戴上胸膛的同时,他已经从战斗民族变成了提心吊胆的“撤退专家”。兵书里说“连败则心战先崩”,换到现实,就是夜里突然惊醒、摸枪号令,半宿睡不踏实。
11月8日的徐州作战会,本该统一部署,却变成众将互怼。邱清泉要守徐州,李弥要保津浦,刘峙镇不住场子,一张大纸上画来划去。黄百韬提出“七兵团立刻拔营向西”,蒋介石电复“暂等四十四军会合”。多等48小时,生死天壤。可军令如山,黄百韬终究没有掉头就走。他对贴身副官苦笑:“站错一步,赔光两万人,值不值?”

当七兵团终于发动,却已被华野诸纵队盯死。运河铁桥被炸,浮桥未来得及架设,退路顿失。黄百韬回到兵团部,擦着汗说:“油灯剩最后一截芯。”几个旅轮流反击,弹药消耗比入围前快了一倍,仍撕不开封锁。电台里,徐州方向只传来“全力救援”的空话,他知道这是客套,更知道援军已被粟裕钉在双堆集那条线上。
11月21日凌晨,总攻号角响起,近两千门火炮一齐倾泻,村庄瞬间成瓦砾。黄百韬转移到油坊村口,抬头看见磨石与榨梁,忽然想到母亲叫他的小名“黄豆”。他对副军长杨廷宴低声说:“黄豆进了油坊,哪还能全身而退?”随后拔出手枪,结束了五十载戎马生涯。枪声落定,七兵团指挥系统如断线风筝,二十五军这个昔日“中央嫡系”只剩一堆枪械和一段番号,被疾风一样的华野步兵碾碎。

有人总结黄百韬的失败,是兵力部署失当;有人说是心理失衡;也有人归咎“蒋家系”内斗。细看这十余场对决,真正压垮他的,是在粟裕节奏里连番跟跑的无力感——一次失算,一段回马枪,一回迟疑,便把整支部队的锐气耗尽。当战术与士气同时跌入低谷,再硬的青天白日勋章,也挡不住碾庄圩夜空下那一声沉闷的叹息。
2
蜀商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